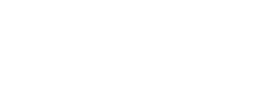和林青霞搭戏的金士杰要来苏州啦,你来吗?
发布时间:2016-12-02
北京保利剧院,赖声川的《如梦之梦》,他和胡歌一个化妆间,出去抽烟、透气时,被粉丝追问:“麻烦问下老师,我送的花儿在胡歌桌子上吗?就是蓝色的那一大捧。哦,在,我就放心了,谢谢谢谢。”
外面的风不小,朋友说,回去吧,他说:“冷一下,精神。”另一批胡歌的粉丝拥到门口,其中的一个小姑娘说:“哇,这不是那谁吗?叫什么来的?老戏骨啊,大神呀。”他听到、笑笑,把烟掐了,进楼门,往化妆间走。
他来大陆发展两三年,街头经常被粉丝脱口而出:“太熟了,这不是那个舒淇的老爸吗?”
去年底上映的《剩者为王》,金士杰在剧中饰演舒淇、一个待嫁女儿的父亲。和自己未来的女婿对谈的一场戏,5分钟的长镜头独白:“三十几年前她来了,我是她父亲,我希望她幸福。她在我这里,只能幸福,别的都不行。”不演而演的深情殷殷,令观众飙泪。
当时拍摄现场的所有人也哭了,可能除了监制滕华涛。据说这位《失恋33天》的金牌导演,当时绷着脸,或者说绷着情感,一脸严肃的站着,“全场的工作人员,除了我和李屏宾老师没有哭之外,其他人都哭了。李老师要把着机器,我要看着监视器,我们需要更克制和冷静吧。”
滕华涛很久之前看过金士杰的《暗恋桃花源》,所以对他的印象停留在江滨柳那个时代。第一次见到本人,是在“金老师”来大陆的话剧结束之后,和剧组的人一起吃了海底捞。
“可能很难用一两句话形容金老师,首先我觉得金老师不老,感觉他还是个很年轻很有活力的一个人。而且作为演员,他基本上演什么像什么,跨度真的挺大的。像这种老戏骨,你只能说他是老戏骨,也不能说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演员。”
和范冰冰的一场戏在怀柔拍,大陆经纪人刘子凡开车去探老戏骨的班。这个年轻女孩子当时的感情出了点问题,72小时没睡的午后高速路,70迈的速度、阳光暖暖的,音响扭到最大声,车窗全开,掐自己大腿……醒过来的时候,她和前面那个大挂车的距离只有几个0.01公分!打轮、急刹车、马路正中央,哭了。
“金老师感觉到我的状态不太好,我就跟他说了一下,包括来的时候,那个车祸也说了一下,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聊,也是喝了点小酒,没有太刻意的。就聊了聊男人女人间那种微妙的关系,情感的不同,宣泄释放的方法。”
对于感情,甚至生死,金士杰有自己的视野:“我年轻的时候,曾经跟教堂关系很深刻。妈妈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只希望我们不要离开上帝。宗教会一直跟你在对话,什么是生?什么是死?我会迎接光明,我要跟黑暗打交道。我不了解它,其实是兴趣,不是信仰。但有时候你搞不好会恨上帝,想跟上帝打架也是可能的。”
1978年,金士杰农专畜牧科毕业,成为一名光荣的兽医,管理着台南县牧场的几千头猪,负责阉割公猪、帮发情母猪找对象、接生、配饲料、治病,一直忙到给猪送终……夜深人静了,可能还会到客厅,实际的猪圈,弹吉他给猪听。
“妈妈生出十几个,当中总有一两只身体特别小、特别弱的,弱到皮肤透明的一样,吃奶吃不上,还容易染上病,注定很快就要死翘翘的。比较不好的方法就是丢到焚化炉,但在那里它们会有一段时间的挣扎。我觉得那个很残忍,在最短的时间内死掉比较好。我就想了好几个方法:往墙上甩一下,或者用脚踹一下,还用过石头,用过砖头。它们身体很小,立刻就会走掉。但是万一你力气不准,还要两次、三次,你心里会特别难受。”
台南牧场位于台湾岛南部的大平原,一眼望不到山。27岁的金士杰提着十几只瘦弱的小猪,走在夕阳下,“把它们处理完毕,身上还带一点血,我就要去洗,洗完,吃晚饭。那个时空之下,自己跟死亡的关系比较辽阔,你会觉得,死亡就是大自然的一件事情。”
金士杰被赖声川称为“台湾现代剧场的开拓者、火车头”,是台湾剧场界的核心创作者,多年来一直从事于舞台剧编导与演出,并参与演出电视剧与电影,曾任教于台北国立艺术学院。他最为剧场观众所熟知的剧场形象,当属《暗恋桃花源》中的江滨柳一角。当然还有《剩者为王》中的催泪老爸,还有《贞观之治》里的魏征,《师父》里的武林老大,《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里的……“别人给你掌声,内心真够骄傲的话,你应该心领就好,不必当真;你真该那么骄傲的时候,自己会知道的,不必在乎别人给不给你(掌声)。”
1986年《暗恋桃花源》第一版,台北小剧场,很多老朋友来看。最后一幕客厅的戏,正赶上窗外的太阳西下,老朋友在台下哭,金士杰在台上落泪,共同伤感着,“当那个老女人走过来,我的心里有些酸、有些疼,有些哭笑不得、有些不舍。我舍不得这么美丽的女人,变得这么老。”
演出巡回到台湾南部屏东老家,父母来看,“妈妈没说别的,就说很好笑,很好玩,看到我儿子在上面,可上镜了什么什么的。我心情上其实有一种,悄悄向他们那个年代致敬的情怀,上场前自己暗暗祷告:爸爸,我来了。”
金士杰的父亲如今一百多岁,除了听力不太灵光外,周身硬朗。中央电视台邀请父子回安徽老家,路上父亲给他讲了自己小时候,在别人婚礼上当花童的故事,“大家一边扔米袋子,一边喊:一袋(代)接十袋(代),十代传百代,轰轰烈烈的。”
从演出20年的江滨柳角色上退下来,青年演员尹昭德接班。当晚演出结束,没卸妆就来敲金老师的门,“卸妆,得找有水、有毛巾的地方,可能他觉得演完戏之后蛮晚了,不好意思来太晚,一头的道具白发就来了……他希望我说一点什么东西,我忘了,我说了些鼓励和建议吧,好像。比如说:你每天晚上,都要把自己轰炸到这个程度吗?是不是有的时候,场次多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稍微用技巧一半、内心一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别过度的赤裸化。”
金士杰对晚辈的关照是全方位的,曾经对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学生、他的爱徒说:“没有问题啊,我们就是好朋友,但如果你允许我说,我会说:你如果不是的话,尽量不要是。” 学生当然没有承认自己是个Gay, 只是笑着问:“老师,为什么你要对我这样说呢?”
隔了一些年,那个学生已经是了,他跟我再对话。我还是跟他说,“你非得是,那就是,那我能劝你的话,我就劝你,99句不要是。因为你们往往特别的敏感、特别有艺术才华,可能会有一些人给你们鼓掌。但这条路很累,很孤单。有的时候会接收到歧视的眼光。你的生活里,会有许多不方便。”
“他如果是我儿子的话,我会心里悄悄的难过。我可能会说,孩子,那是个少数族群,是边缘人,社会会给你很多不方便。我没有办法陪你走一辈子,你会活得比较孤独,会让爸爸心疼……但是简而言之,一个父亲可能会说:孩子,我知道那条路很辛苦,它与对错无关,我只觉得它很辛苦。”
当年作为儿子的金士杰,屏东农专畜牧科毕业后,想去台北,“去做很重要的事”。妈妈怎么劝都不听,就去高雄和自己的爸爸讲。父亲听不懂“剧场”、“导演”这些词汇,不明白孩子将来怎么过日子?“他最后什么都没说,只是站起来从柜子的夹子里拿了亲戚的电话号码和车票给我,就去了厕所。从后面看他弯腰、捏着鼻子,一定知道嘛,他哭了。他好失望,他一直希望我找份工作,结婚生子,安分过一生。”儿子金士杰,暂时放弃台北那些“很重要的事”,去了屏东老家边上的台南县牧场,养了一年半的猪,“我用行动告诉他们,我是个会做正经事的、规规矩矩的人。”
混过猪圈、恨过上帝的金士杰,生活将他的演技打造得炉火纯青。对舒淇的那段台词,成为父亲节的经典献礼,在网上疯传。
“对,她不该为了父母结婚。他不应该在外面,听什么风言风语,听多了就想着要结婚。她应该跟自己喜欢的人白头偕老的,要昂首挺胸的、特别硬气的。憧憬的,好像赢了一样。有一天突然带着男方,出现在我面前,指着他跟我说,爸,你看,就这个人了,我非他不嫁。你看我都真真切切地想到了,我有什么理由不真真切切地等着她实现。那件事情什么时候到来我不知道,但我要跟她站在一起。因为我是她的父亲,她在我这里,只能幸福,别的都不行。”那个老父亲缓缓摇了三次头,含着泪。镜头切换到女儿舒淇的脸上,脸颊挂着泪珠,“爸,我答应你,我会幸福的。”
有粉丝或者记者,把这句台词打印出来,向他讨教其中的泪点营造。金士杰从包里摸出眼镜盒,打开、带上,细细地从头到尾念诵一遍。那种恭敬和专注,就像第一次看到、读到一样,“加上‘他妈的’就很好念。你懂不懂? -------她不该为(他妈的)父母结婚。他不应该在(他妈的)外面,听(他妈的)什么风言风语,听(他妈)多了就想着要结婚----你的情绪要到达那种状态,只是没有说出来。你想,几乎愤世嫉俗到那个程度,但你不能只有愤世嫉俗,你必须是一个多情的、温暖的谩骂。”
春节前的家庭聚餐,金士杰在笔记本电脑上搜出这段视频,连上电视,大家重温。爸爸耳背,听不清,只是看着电视笑着。排行好二的金士杰对身边的四妹说:“小伟,说这段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想的是你和父亲。”四妹金世伟不清楚二哥为什么想的是自己?她只记得小时候,因为学习好,总被爸妈宠,也总和爸爸犟嘴。有一次和爸爸冲突后,夺门而出。晚上回家后,二哥告诉她:“你走后,爸爸就悄悄去窗口看,一直看着你出了巷子口,怕你出什么问题,担心你磕了碰了什么的。”
金士杰念出那段台词的时候,想的确实是四妹,但心底映出的却是另一个画面:“四妹结婚,我要去拍嘛。摄像机扛在肩上,喜宴上拍到妹妹眼红,我也红,镜头转过去,拍到爸爸眼红,我又红,其实(表达的)是那种不舍。”
女儿总是要嫁的,父亲总是要老的,因一段感情曾经誓言终身不婚的金士杰,也在2009年的春天,以57岁的新郎官身份迎娶了32岁的学生涂谷苹。台北亚都丽致饭店的婚宴,一桌家人、两桌朋友。新郎难得一件的一身西装,新娘水蓝色的低胸小礼服。
“什么时候转念头接受婚姻,或者是生孩子?我在开窍,很多问题都不需要内心问答了。人就是大自然中的一种元素、一种状态,老了就是老了,病了就是病了。没有什么对和错,太阳出来或者太阳没出来,被云遮到了,这不是错,就是遮到了。你觉得树叶的掉下来有什么错?你会对它说:丢人!人家还没掉,你掉干嘛?”同样的问题,台湾记者得到的答案是,“到了某个巷子,就会自然向左转。”
为了配合新片上映的宣传,金士杰老师会很“自然的”参与综艺节目《康熙来了》,会被问一些很搞的问题,诸如“老师长没长过痔疮?”、“会不会被小自己25岁的年轻妻子质疑性能力?” ……然后,这位60多岁的老戏骨会一本正经地说:“(她)不会直接告诉我怎么样吧。只是用她的各种肢体动作,让你觉得,今天挺好。”现场观众哄堂大笑的时候,金老师还会补充一句:“也会看A片呀,但有些演员太不敬业了,看着很好笑。”说完了,脖子向左梗在那里,抿嘴笑等小S的下一个问题。
作为台南牧场曾经的阉猪大王,27岁的金士杰,会很熟练的为小猪做绝育手术,“后腿儿一提、小刀一划,小睾丸隔断、碘酒一涂……一个下午,睾丸就小山一样堆在那儿。葱姜蒜一放,就点酒,很好吃。”
拍戏的间隙,对于好奇那段经历的晚辈,他会不厌其烦的津津乐道,每一个细节,“猪妈妈的第一次比较不会使力气,所以就要帮它。如果它太胖了,运动少,那条生孩子的路就会特别窄。我们就把指甲都剪干净,整只干净的手伸进去。它会觉得痛,会闭起来,你要等到一会儿,等它重新松开,再慢慢进。弯弯曲曲的,很漫长,终于摸到几个滑溜溜的小伙子缩在里头,在外面欠了债不敢出来似的,要一个个把它们抓出来。有时候脱手、滑了,再抓住。通常第一个大个的出来,后边就跟着出来,而且妈妈一旦知道这个力气怎么用,就比较好办了……虽然蛮辛苦的,但是你看着一家老小躺在这个草房里面,吃奶干嘛的,心里还是蛮安慰的。”
这个在台湾戏剧界被称为“金宝”的老顽童,青年演员周一围眼中“那个修行甲子的老妖怪”,他的轻松、自然,那种顺应生活的温暖,几乎与生俱来。
天下那么多优秀的男人,金宝自认的可爱之处都来自于父母,“我妈妈,简单的形容她这个人,就是纯,纯的让人惊讶。对于人的是非,对于社会,对于人活着的需求,极简单。简单里有一种美感在里头。我觉得像天使,或者像婴儿。经常会想,人这么大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我爸爸?肉麻。我喜欢他的肉麻。他跟你见面,抓着你的手,如果女生,他也是这样。一抓抓好久。女生就开始抽手了,抽不掉。他对人的好,是那种一发不可收的好。他其实是非常理性,懂得礼节的人,但他心中有那种热度,那种情感。非常可爱,非常原始,是人身上的那种很骨髓的东西。妈妈身上的那种纯,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东西。两样东西都有些蛮,天赋异禀,是那个人的根性。”
“金老师的内功、神华都是藏着的”,1982年出生的大陆演员周一围,是金宝的忘年交,每次剧组拍戏的空档,会提瓶牛栏山二锅头到金老师的房间聊半宿,聊聊曾经合作的《绣春刀》、《盲人电影院》,聊聊金宝在《一代宗师》中对王家卫的理解,“有时候拍到凌晨三点,小年轻都已经涕泪横流了,金老师还相当精神,这么大岁数了,还蹦跶的相当欢、精力依然旺盛,绝对一个修行甲子的老妖怪。看起来那么一个人畜无害的状态,永远恭着、缩着,哆哆嗦嗦的安静内敛,一个典型的民国时期的台湾老头。”
(原文刊载于2016年4月《男人装》杂志,图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