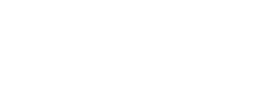【媒体聚焦】苏芭《唐寅》:现代意识照亮古典题材
发布时间:2017-09-11
9月7日,苏州芭蕾舞团推出十周年原创新剧《唐寅》。舞台中央,一件红袍,裹挟着唐寅的命运,功名与自由的冲突,几乎纠缠了他的一生。——这是苏芭艺术总监李莹和潘家斌眼中的唐寅:他是放浪形骸的风流才子,也是怀才不遇的悲剧人物。
10年前,芭蕾舞艺术家潘家斌、李莹伉俪从美国回到家乡苏州,协助苏州文化艺术中心组建苏州芭蕾舞团。2007年苏芭成立以来,不断推出新剧目。《唐寅》是他们编创的第七部大型芭蕾舞剧,也是继《西施》之后的第二部本土题材作品,获得江苏艺术基金和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关于唐寅,也许大多数人只知道《唐伯虎点秋香》,但是在他的家乡苏州,唐寅的跌宕人生却几乎家喻户晓。人们知道,秋香只是传说,与唐伯虎有关的是沈九娘。舞剧需要冲突,而《唐寅》不像《西施》那样有明显的戏剧冲突,如何在舞台上表现人物?在决定做这部芭蕾舞剧之后,李莹和潘家斌搜集了大量资料,却仍然有些困惑。2015年,在苏州博物馆的唐寅特展中,他们看见了唐寅的《韩熙载夜宴图》。李莹说,自己当时眼前一亮,画中的一袭红袍鲜艳夺目,而唐寅一生的悲剧,不就是没能穿上那件红袍吗?这幅唐寅摹写的画,让李莹找到了解读唐寅的密码。在芭蕾舞剧《唐寅》中,红袍是功名的象征,贯穿着全剧;韩熙载甚至从画中走了下来,成为舞台上一个亦真亦幻的人物。
苏芭究竟会在舞台上呈现一个怎样的唐寅?我们又应该如何认识艺术作品中的唐寅?在《唐寅》首演之际,苏周刊特邀苏州芭蕾舞团艺术总监李莹、舞蹈评论家许钰民、文艺评论家陈霖,围绕芭蕾舞剧《唐寅》对话。让我们跟随他们,走近苏芭舞剧《唐寅》。

芭蕾舞剧《唐寅》剧照:舞台上的两个唐寅。
唐寅总是在展示极端的两面
苏周刊:其实一直存在两个唐寅,传说中他是一个喜剧人物,事实上他可能是一个悲剧人物,苏州芭蕾舞团将会呈现一个怎样的唐寅,是想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还是塑造你们心目中的唐寅?
李莹:在准备做《唐寅》这部芭蕾舞剧的时候,我们相信《唐伯虎点秋香》的那个唐寅不是我们想要呈现的。那么唐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我们花了一年多时间来慢慢探索。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我们觉得《唐伯虎点秋香》那个唐寅是存在的,是他的一面,是他的表象;而另一个悲剧唐寅也是存在的,是他的内心世界。唐寅并不是平白无故地在五百年来的历史上留下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一定有什么原因。在对唐寅的各方面研究和了解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要在舞台上表现一个我们所了解的唐寅。这究竟是不是一个准确的唐寅?谁都没法说清。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我们舍弃了才子们饮酒作乐的情节,虽然这可能也是他人生比较重要的部分。但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怎样把他的内心世界展现给观众,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内心世界的唐寅可能并不真实;可能表象的唐寅才是他的本我,他本来就很风流,并不是那么在乎功名。但是内心世界的唐寅——大家所认为的一辈子很痛苦很失败的悲剧人物,我觉得,是社会造成的另外一个唐寅,在他的内心世界,他放不下他的功名,因为他承担了父母家庭加给他的义务,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你说风流的唐伯虎是他的表象,但可能反而是他的原形,是他的本性,所以他一直很挣扎。正是因为上千年来的历史文化的影响,我们现代人才会认为他是个失意的悲剧人物。我个人认为他真实的一面反而是他的本我,但你也可以说他放浪形骸的表象是为了遮盖他的内心痛苦。我们在舞台上呈现了两个唐寅,一个代表现实,一个代表他的内心世界。
苏周刊:这是您对唐寅的理解,我也想问问两位评论家,你们怎么理解唐寅这个人物,你们期待在舞台上看见一个怎样的唐寅?
许钰民:目前我们从大量的娱乐作品当中所看到的,是快乐的唐寅、喜剧性的唐寅,但是真正的隐藏在后面的人生悲剧,是要深入地了解历史文化以后才知道的。唐寅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刚才导演说的有点道理,他的本性还是我们所看到的潇洒的那一面,但社会和家庭的负担使得他的本性扭曲了。以他的资质,应该生活得很好,他才华横溢,诗书画都很出色,但是现实跟他的性格形成了强烈冲突,造成了他的悲剧,我们以往的文艺作品揭示得不够,所以我很期待看到苏芭的《唐寅》。
用芭蕾舞剧表现唐寅,这很不一般,苏芭是用一种外来的语言说中国故事。我们习惯于听中国话了,突然听到一个半洋半中的人说这样的语言,恐怕观众有点难以接受。就艺术作品来讲,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曾经说过,一个作品必定有四个要素来显示:第一个要素是世界,第二个要素是艺术家,第三个要素是艺术作品,第四要素是观众。那么,作为一个用西方语言来诠释中国古典故事的作品,其中就存在一个关于艺术作品怎么来揭示客观世界内容的矛盾,所以观众能不能理解,可能还有一个过程。芭蕾舞剧《唐寅》,我认为是一个大胆的、目前在中国还不多见的尝试。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也做过这样的尝试,苏芭的《西施》也做了这样一个工作,今天的《唐寅》在继续尝试,对此我是抱着很大期待的。
陈霖:关于唐寅这个人物,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并不存在我们通常所讲的真实,他就是塑造出来的。苏州芭蕾舞团的《唐寅》是通过芭蕾舞这种艺术形式塑造出来的,这个唐寅和以前我们了解的、印象中的唐寅有什么不同?可能这就是艺术更为感兴趣的。刚才李莹老师说,也许通常所认为的唐寅的内心世界更假,而外表恰恰是他的本真。我想,这个假和真是相互映照的,可能恰恰是这种相互映照、互动、分裂的过程,让一个我们以前所忽略的、没有看到的唐寅,呈现在我们面前。这肯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唐寅。
李莹老师他们表现的唐寅的人生,我觉得是烦恼人生。唐寅有一首诗写道:“人生七十古稀,我年七十为奇。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中间只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算来只有二十五年在世,受尽多少奔波烦恼。”我觉得李莹老师他们要表达的,可能就是这种烦恼。烦恼的极致便是他那种分裂,因为内在的自由奔放的需求和外在的各种压迫没法和解,最后就是崩溃。唐寅总是在展示极端的两面,特别具有张力,一方面纵情声色,一方面又皈依佛门,“六如”的“空”和他在声色之中的沉溺,是非常矛盾的,而这恰恰就构成了他这种非常真实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代人理解唐寅是有可能的。
唐寅自由的内心世界,需要富有张力的现代舞来表现
苏周刊:李莹老师提到过为了做芭蕾舞剧《唐寅》,特意和潘老师一起去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参加冬季特训,为什么要寻找现代舞的语言来表达唐寅这个题材?
李莹:其实我们在《西施》的舞蹈语汇里面已经开始有了一点点现代语汇。《唐寅》需要更大的自由,更多的发自内心的舞蹈语汇。唐寅自由的内心世界,需要富有张力的现代舞来表现。传统芭蕾动作规整,很表象,它是美的,而现代舞比较容易表达自己内心的世界。在做《唐寅》的时候,你不是所有时候看到的都是现代舞,比方说在“夜宴图”开始的时候,要表现一种华丽的想象,芭蕾舞的语汇会更多一点;但一旦切入到内心世界的时候,就切入到现代舞的语汇。当然我们芭蕾舞演员跳出来的现代舞并不见得和现代舞演员跳的一样,这本身就是一种结合。通过两种舞蹈语汇的切换,内心世界的表达在观众面前清晰可辨。
从一开始准备做《唐寅》,我觉得唐寅是我们所有做过的题材中最难做的。很幸运,我们看到了唐寅的《韩熙载夜宴图》,从我们自己的一个非常主观的想象,到后来客观的发现,它确实是我们所认为的他的内心世界的写照。这为我们在艺术处理上打开一扇门。芭蕾舞在这里只是一种语汇,最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剧怎么来结构,有什么自己的特点。五年前做《西施》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这是芭蕾,要突出它和民族舞剧的不同。而这次我们的重点不是用芭蕾来突出它的不同,而是在创作形式上、创作特色上怎样更加有新意,在与众不同的前提下至少先做到不同于我们以往的作品。
陈霖:我想补充一点,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一直有人在摹制,我从你的解读中获得了启发,唐寅摹这个画,可能也因为《韩熙载夜宴图》的内容跟他内心、生平有某种联系。韩熙载是一个官员,他的纵情声色是一个表象,另一方面就是郁郁不得志,难以实现自己。画的内容跟唐寅本人是相契合的。我觉得这点上很聪明,你注意到“夜宴图”中的红色官袍,这样就获得了一个解读唐寅的密码。
李莹:我觉得在编《唐寅》的时候就像那部名为《达·芬奇密码》的电影一样,一直在不断解读他的诗画内容,发现每一个蛛丝马迹,来探索领悟这个距我们五百年之遥的唐寅。真的是这样!
陈霖:从韩熙载生活的五代到唐寅,已经过了五百年,从唐寅到今天又经过了五百年,某些东西是不变的,就是人性深处的那种冲突的结构形式,甚至包括冲突本身,那种外在的负担与内在的要求、对自由的向往,才情的挥洒与功名的引诱、与求售的心切,古代文人身上的这些东西与现在是相通的。所以这也是你能够用现代芭蕾的语汇去重新诠释它、是我们现在的观众能够理解它的一个重要的条件,这就是现代意识;把人放在最前端,不是故事,不是花里胡哨的那些东西,而是把“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去追问,这就是用现代意识来照亮一个题材,或者说,一个题材一下子在现代意识的照亮下获得了新的存在,我觉得这可能是芭蕾舞剧《唐寅》特别大的意义所在。
许钰民:我同意陈老师的看法。关于唐寅性格的本真,其实无所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艺术作品是虚拟的。隔着五百年的距离,我们怎么能够还原到过去的本真呢?再说,你掌握了现代语言,他掌握了古典语言、民族语言,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待历史人物,关于真实与否的问题,我向来认为,艺术家只要能自圆其说那就成立了。另外,古典芭蕾是程式化的,作为今天的芭蕾舞团,而且你们又受到了美国现代芭蕾舞的影响和熏陶,所以肯定会追求那种挖掘人的心理的手法来创作《唐寅》这个作品。说实话如果按照古典芭蕾来表现,现代人不大喜欢看,显得比较陈旧,现代的作品、现代人的诠释就应该用现代的语言去做,我完全理解你们为什么要去学习现代芭蕾舞的表现手法。
苏周刊:从导演的角度看,最希望观众关心和注视的是剧中哪几段舞蹈?
李莹:其实每一个舞段对我们这个舞剧都是必然存在、必须存在的,中间只有极少部分的铺垫。我希望观众更关注唐寅内心世界的表达,从这个角度讲,确实有几个舞段。比方说一开始,舞剧由唐寅入狱切入,这个舞段是他处在人生最低谷,遭受精神肉体双重痛苦的状态中。一幅展开的画卷,一件被父母高高挂起的红袍,他从黑绸中赤裸地滚出来,仿佛生命从此刻开始。红袍成为一个线索,他在监狱里回忆,展开内心世界,回忆自己和父母是怎样期待能够早日穿上红袍,功成名就的;他在青楼和沈九娘见面,沈九娘是他的红颜知己,能够理解他的痛苦,他画《韩熙载夜宴图》,专注在那个穿着红袍的状元与韩熙载身上,这条线索延伸下来了;一直到他选择远离仕途,与沈九娘相爱,隐居桃花坞,但红袍仍然在幻境中影响着他。红袍和沈九娘之间,就像仕途和自由之间,难以选择。我们在双人舞之后设置了一个场景,通过舞台呈现三组人物关系的切分:父母拿着红袍希望唐寅穿上;回放“夜宴图”中韩熙载(这个角色有双重寓意,也指之后的宁王)和红袍之间的关系;唐寅与九娘之间的难舍,最终唐寅选择随着红袍而去,追随宁王。当唐寅发现宁王叛乱后,在这一舞段中内心世界的唐寅和红衣唐寅同时出现,内心世界的唐寅作为旁观者看着现实世界的唐寅,直到最后,把唐寅的红袍脱掉,裸奔,仕途之梦彻底毁灭。
陈霖: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富有现代感,这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不断地接触我的面具,接触我的表象,发现究竟我是谁。这是一个现代人感到特别困惑的问题,也是觉醒的前提。从内心冲突来讲,我们可以把这个剧归结为自我探索、自我发现、自我毁灭、在毁灭中发现的一个过程。
每一段阿沃·帕特的音乐,都是我们希望观众关注的《唐寅》片段
苏周刊:李莹老师提到过,这部舞剧中用了很多爱沙尼亚现代作曲家阿沃·帕特的音乐,中国传统故事、古典人物和现代音乐,这部舞剧是如何协调这三者的?
李莹:世界上很多现代舞编导都喜欢这个作曲家的作品。我们决定做《唐寅》的时候,第一个跳入脑海的就是他的作品,因为他的生平和唐寅有相近之处,所以他的作品也有很多内心的挣扎,在平静中又不平凡。我们在舞剧中多处用到了他的作品,同时也运用了巴赫的作品,当时很想寻找一些接近唐寅时代的西方作品,巴洛克风格进入我们的视线。而有意思的是阿沃·帕特的曲子受巴赫的影响很大,在巴赫的作曲上创新,就像我们要把《唐寅》“创新”一样。在《唐寅》的最后一段“绝笔诗”中我们用了他的曲子,非常平静,音乐在不断地重复,就像他脑海中不断闪现的一生一样,这是这个舞剧中用来表达唐寅最最安静的一段音乐,当人生走到尽头,他是平静的从容的,觉悟地离开。
陈霖:规律之中的一点变化,一下子抓住了你,触动了你,这种音乐的特点,在《唐寅》的表现中,具体来说,有哪些契合之处?
李莹:我们选择阿沃·帕特的几首曲子,并不是很相近的作品。一开始我们用的他的一首曲子,像教堂钟声,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寺院的钟声,给观众一个非常厚重的感觉。“韩熙载夜宴图”这一场中,你会听到敲三更的声音,就是这么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他的内心世界是翻滚的,这也是非常好的一段音乐。在宁王那段,到最后,唐寅发现身边都是叛军,所有的人脱掉红袍露出黑袍,跪在宁王面前,那首音乐太棒了,只有红衣唐寅非常困惑地转过脸看着内心世界的唐寅,这个唐寅把红衣唐寅的红袍脱掉,推出人群不停地裸奔。这时候音乐多次规律性的“哐”!不断地爬起、崩塌,追求仕途的那个唐寅最终倒下了。这段音乐非常典型。其实每一段阿沃·帕特的音乐,都是我们希望观众关注《唐寅》的片段,这些片段都是内心世界的。而巴赫、埃尔加的,就更唯美。“落花诗”那一段,我们用了一段非常唯美的埃尔加的音乐来表达唐寅与沈九娘的爱和别。
苏周刊:在你们作品里,《唐寅》是不是用现代舞语汇最多的一部?
李莹:我们并不想让它成为大家所认为的古典舞剧,其实在《西施》上我们就已经想要突破。
许钰民:他们从美国回来就预示着不能走古典芭蕾之路,也不可能走,因为他们接触了美国的现代舞蹈创作思维和手段,基本上形成了他们的风格。
李莹:说句实话我们差点就让唐寅穿上西装了。也许可以大胆一点,走得更远一点,不是不可能的。我们曾经想过,为什么不能完全抛开唐寅的时代束缚?但是毕竟我们在做一个苏州的本土作品。现在《唐寅》的服装设计概念是结合现代时装的理念,很简洁,并不写实。其实《西施》也是这样,没有人说你这造型不符合我们心中的西施,因为现代观众还是很开放的,没有人来质疑这一点。
在艺术创作上,我们希望能够引领观众,而不是迎合观众。